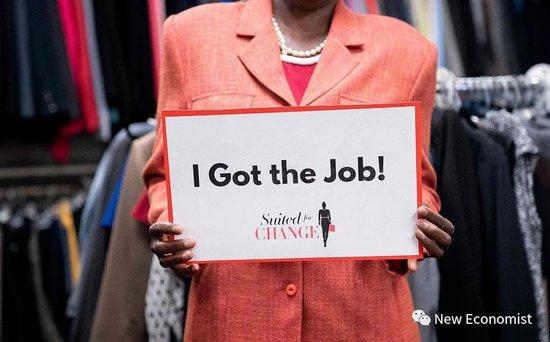来源:澎湃新闻
转自: New Economist
克劳迪娅·戈尔丁:新冠疫情对美国女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性别经济学、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在其新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克劳迪娅·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第一组:成家或者立业;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先立业再成家;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兼顾,追溯了她们的工作和家庭的演变历史。本文为该书后记的部分内容,原题为《被放大的旅途终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任何时代都充满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时期更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特点。在新冠大流行开始之际,美国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今已经大幅下降。不过,很多工作和小企业仍然处境艰难。在本书写作时,美国的公立学校尚未完全开放,日托中心时开时关。安全有效的疫苗终于有望广泛提供,但还并非人人均已接种。正常的生活似乎指日可待,但是这个“可待”时间却总在变化。
新冠疫情是一场灾难。它夺去生命、夺走工作,并将影响未来数代人。它暴露了种族、阶层和性别在谁被感染、谁死亡、谁必须到一线工作、谁可以学习、谁负责照顾孩子和病人等方面的不平等。它把国民分成了富人和穷人。这俨然是一面令人惊慌的放大镜,放大了父母的负担,揭示了工作与家庭照护之间的权衡,也加剧了本书记载的五个群体在旅途中遭遇的大部分问题。
新冠大流行对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往往是工作和家庭的重要劳动者。她们当中,有牙牙学语宝宝的新晋妈妈,有百无聊赖接受在线教育的青少年的年长妈妈,有目前依靠食品供应站生活的贫穷单身母亲,有争取升职机会的高学历女性,还有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有色人种女性,在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之前,她们早已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
我们正历经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一线辛劳的工作人员堪比战时的士兵。但是,以前从不要求一线工人把危险带回家里;我们从不需要关停经济以促其重新运转;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影响从未超过男性;护理部门从未如此鲜明地与经济领域紧密连在一起。今天,女性几乎占据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我们必须确保她们不会因为照护问题而牺牲工作,也不会因为工作而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
本书关注女性大学毕业生对事业和家庭的追求;以她们作为样本,是因为在过去的120 年间,她们最有可能实现这个双重目标。她们曾经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前占年轻女性的比例不足3%。如今,女性大学毕业生几乎占美国20多岁女性总数的45%。
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焦虑和不满日益突显。充斥报纸、新闻推送的关于第五组年轻成员未来的预言耸人听闻:“新冠大流行将‘使我们的女性在职场倒退10年’”,“新冠大流行或将伤害一代职业母亲”,“新冠病毒如何导致女性劳动力发展退步”。新冠疫情时期,需要照顾孩子和其他人的人们都在奋力投入更多时间,发表学术论文,撰写各类简报,在Zoom视频会议上应对要求苛刻的客户。
根据上述预测,眼下,那些原本有望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人可谓突然失去支援。就像美食博主黛布·佩雷尔曼(Deb Perelman)说的:“让我把大家默认的大声说出来:在新冠疫情的经济形势下,你只能要么带娃,要么工作。”第五组女性会不会重蹈覆辙,做出和第一组一样的妥协?
毋庸置疑,女性比男性更易感知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出现“女性衰退”(she-cession,又译“她衰退”)一说的原因。但是,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女性大学毕业生维持就业的能力更强,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教育使她们有能力居家工作,而这保护了她们的健康和就业。
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秋冬季有学龄前孩子(5岁以下)的25-34岁女性大学毕业生妈妈的劳动参与率仅下降1.2个百分点(基数为75%)。但是,有小学和中学年龄孩子(5-13岁)的35-44岁母亲的这一比率下降了4.9个百分点(基数为86%),降幅颇大。而非大学生群体无论有无子女,因为受雇于最脆弱的行业,劳动参与率更是大幅下滑。
上述画面貌似并不符合头条新闻渲染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但数据确实显示,裂缝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扩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许很困难,缺失工作经验还将影响日后的收入。即便对于保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也会问:在选择获得合伙人身份、终身职位和首次晋升方面,母亲是否处于不利地位。在学术界,过去一年里母亲们发表的论文比没有学龄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少。此外,数据没有披露众人的沮丧和挫败,对许多人来说WFH(居家办公)意味着“在地狱工作”(“Working From Hell”)。
不满情绪
我们探讨了一个世纪前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抱负,她们面临着要家庭还是要事业的选择,她们面临着诸多禁制,哪怕身处繁荣时代。几十年间,障碍不断消除。我们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她们日益渴望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她们明白,必须遵守这一顺序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后我们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她们在教育上得到进一步提升,职业机会也有所增加,能够更率真地舒展抱负。她们公开表示想收获事业和家庭的成功,更是希望同时达成二者,不需要依循特定的顺序。过去数十年里,她们已经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但是,早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国的近十年前,在#MeToo运动分水岭出现的几年前,女性已经开始广泛表达不满情绪。从新闻媒体上搜到的“性歧视”(sex discrimination)、“性别歧视”(gender discrimination)等短语表明,人们对工资不平等的不满和对性骚扰的反抗日渐加剧。
2010年之后,几起备受瞩目的事件登上新闻头条,譬如鲍康如起诉雇主凯鹏华盈性别歧视,男女职业足球队员之间的薪资差距,等等。好莱坞、华尔街、硅谷赤裸裸的性别工资差距案例也被曝光。随着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出现诸多问题,尤其是《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中传出的猥亵言论以及这些言论对选举结果明显缺乏影响力,女性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些事件的报道引发了20世纪性别不满的第二个巅峰时刻(套用新闻报道的表述)。而第一个高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
60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几乎绝口不提“性歧视”;几十年后,“性别歧视”一词才渐为人知。大约在1971年,关于“性歧视”的文章开始暴增,到了1975年,包含该词的文章触及一个高点。接着,这个词的使用断续减少,并在35年后的2010年左右降至1975年水平五分之一的最低点。
但是,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不满情绪突然翻腾一样,它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次喷涌,一直攀至历史最高水平。#MeToo运动和Time’s Up运动推波助澜,却也止于2017年底。甚而早在#MeToo运动成为女性反抗和抵制屈辱境遇的标志之前,不满情绪已经日益激昂。
20世纪70年代初不满情绪高涨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时性别工资差距实在巨大。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59%,并且该比率长时间滞留在这一糟糕水平。女性始终被排除在各种社团、餐馆、酒吧之外,甚至才刚刚获准入读国家级的精英院校。历经了从民权到反战的抗议运动时代,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终于保障女性在教育和体育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些时光令人振奋,解放女性和意识觉醒团体遍地开花。女性总算有了发言权,她们用它大声抒发不满。
然而为什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正当女性在就业、收入和教育领域斩获辉煌成果时,新闻文章里又流露出类似程度的不满和沮丧?
因为人们的期望提高了,愿望也改变了。女性,尤其是女性大学毕业生,预断自己能够拥抱事业和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坚称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应该得到公平对待。大学毕业生则渴望获取和男性配偶同等的成就。大家开始憧憬不仅要实现工作场所的两性平等,还要实现家庭的夫妻公平。
正如我们所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工人的性别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但从90年代起,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收入差距开始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意味着顶层人群正在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攫取利益,而在这个稀有群体中,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奇高。
贪婪的工作变得越加贪婪,承担照护责任的女性不得不挣扎着跟上。
照 护
以上一切,早在“前新冠时代”已经出现。2020年3月,非常紧急和突然地,家长们被告知学龄孩子要待在家中。托儿所全部关闭。我的哈佛本科生都去度春假了,之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返回学校。员工被要求居家办公,除非国土安全部认为其“不可或缺”。至此,整个美国进入“新冠时期”。
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的经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经济衰退本来不致如此。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务行业,一直免受离岸外包、国外贸易冲击和自动化的影响。可如今,酒店业、旅游业、个人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的服务岗位遭到沉重打击。在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世界,面对面服务行不通了,何况室内工作比室外工作更不利于健康。建筑业倒是出现了反弹;大多数制造业也表现良好。最受影响的女性群体是单身母亲和大学学历以下的女性。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在飙升,同时劳动参与率日趋下降。
和前新冠时代一样,大学毕业生父母比其他人过得轻松,毕竟他们更有能力居家工作。根据基于职业特征的估算,新冠疫情之前,62%左右的大学毕业职业女性(25-64岁)可以居家工作。2020年5月当前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约60%的女性做过远程工作,与男性同行的比例大致相同。在接受了一些大学教育的女性中,42%的人能够居家办公,而没上过大学的女性的这一比例只有34%。2020年5月,声称从事远程工作的非大学毕业女性的实际比例仅为23%。
鉴于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职业,他们已经做好封锁的准备。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注定是重要一线工人的大多数,要么被休假,要么被解雇。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劳动力中始终最低。2020年4月,即疫情暴发后经济最低迷的月份,全美失业率触及两位数峰值,35-44岁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另有5%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非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失业率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达到17%,另有10%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
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工作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居家工作仍意味着员工被假定可以在非正常时间工作,可以在客户或经理希望完成工作时工作。但居家工作可能会不断受到干扰。
对于大多数有学龄前和学龄子女的家长,在新冠疫情期间,家庭对时间的需求是巨大的。每个人在家里都要更加努力。对有孩子的人来说,疫情期间家成了日托中心和学校。而如果配偶或孩子生病了,家就是诊所和医院。个人在有偿工作上不间断工作的时间已经急剧减少。
在本书写作时,美国正处于我所说的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混合期,因为从许多方面看它属于“后新冠时代”,但其实它仍停留在“新冠时期”。一些公司、办事处和机构已经营业,一些学校和日托机构也已开放。然而很多学校只是部分开学,有些学校仍然完全远程授课。对于有孩子的夫妇,学校部分开放或远程上课意味着孩子要待在家里,运气好的话,会有一位家长居家相陪,督促学习。如果历史抑或我们刚刚经历的旅程具有参考意义,那么这位家长很可能就是女性。
新冠疫情时期,照顾孩子的时间究竟增加了多少,带薪工作的时间又减少了多少,这在具有全美代表性的大型样本中尚不得知。有关时间使用情况的常规研究譬如“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已于2020年3月暂停,直到5月才重新启动。这些数据在一段时间内将无法公布。
根据“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我为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孩子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样本家庭”创建了“前新冠时代”(疫情流行前年份)的评估。封锁前,样本家庭的母亲平均承担61%的育儿工作(她们还包揽了近70%的食物准备、清洁、清洗等家务)。至于没有工作的同类型母亲,这一比例为74%。
疫情封锁期间,孩子暂停上学,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服务有限,很多看护人员被迫休假,父母总的投入时间大大增加。家长接替了老师的位置,监督孩子的上学时间,辅导他们做作业;老师则忽然成了遥远的屏幕影像。
疫情封锁对样本家庭母亲的直接影响是,她们与孩子相处的总时间翻了一番。但实际上,双亲家庭中母亲照料孩子的比例有所下降,因为父亲也待在家里,他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封锁前增加了很多。2020年4月的调查表明,母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增加了1.54倍,父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增加了1.9倍。此外,每位至少有一个小学或初中年龄孩子的家长,每周额外分配大约4个小时督促孩子的远程学习。最小孩子在上高中的家长,每人多增加约2个小时。
毫无疑问,在封锁前,照顾婴儿需要的时间最多。封锁之前,有婴儿的夫妇每周花42小时照顾宝宝;其中母亲的照顾占66%。封锁期间,每周的总时间激增至70小时。但是,妈妈照护新生儿的时间虽然从28小时增至43小时,所占的比例却降到了61%。
对于最小孩子上小学或中学的家长,母亲每周花在照顾孩子及其远程教育上的时间大约从9小时增至17小时。不过,和前述情况一样,封锁期间父母双方的照护时间均大幅增加,而母亲承担的育儿和远程教育占总时间的比例从近60%降至略高于50%。封锁似乎有利于夫妻公平,因为女性占育儿和远程教育总时间的比例下降了,男性的相应比例上升了。也许当一切结束后,男人们会希望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并愿意为家庭贡献更多的时间。但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尽管双亲家庭中母亲占据的照护时间份额有所下降,但育儿和家务劳动的总负担依然沉重。对于父亲,这几乎同样不堪重负。可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日常家务,如做饭、洗衣等,她们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据英国一项调查估计,2020年4月,在职母亲在一半的带薪工作时间内受到打扰。
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时期,当部分学校、众多托儿所和某些公司重新开放后,情况有变化吗?由于某些儿童托管服务和学校教育已经开放,儿童保育总需求应该介于新冠时期的最高峰和前新冠时代的较低水平之间。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的总育儿负担大致保持不变,而她们占总负担的比例增加了。原因是,美国所有学校和托儿所的开放比工作场所会更审慎;结果,一些员工得以恢复以往全部或部分工作时间。可是,总得有人在家照顾孩子。女性从更多托儿服务和学校开放中获得的好处,被配偶时而重返工作岗位抵消了。
这种好处既不均衡,也不稳定。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日托机构已经基本重启,许多家庭也重新雇用了被迫休假的儿童保育员。但即使进入2021年3月的学年后期,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美国许多最大的学区仍未完全开放,尽管每个学区都有“很快”全面放开的打算。一些学校开放后又突然关闭,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遣送回家。心力交瘁的家庭最终在家长或有偿家教的带领下,组建了或真实或虚拟的“学习舱”(learning pods)。
随着公司、办公室和各类机构重新开放,工人们可以像从前那样离家上班(只是比以前略微谨慎)。但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学校依然部分远程上课,那么一位家长仍需要部分时间在家,也即至少还得留一人居家待命。
每位家长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想回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工作的人可以了解更多情况,接触更赚钱的客户,参与更有趣的项目;还可以和同事面对面交流,更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扰,远离孩子学习乘法表的喧闹。
夫妻双方可以继续在家上班,就像伊莎贝尔和卢卡斯,各自进入高度灵活的岗位。但果真如此,他们也会跟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一样放弃某些收入。假如家长中一方居家工作,一方回到办公室,他们的收入或许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但那些最终回归办公室的家长,哪怕只是部分时间回去,也将有所获益。虽然大家的猜测很多,但我们尚不清楚这场破坏性的强制实验会带来什么结果。
再一次,正如我们从历史中了解的,那个将恢复新版“旧常态”、在办公室工作(即便只是小部分时间)的家长,很可能是男性。但这还是未知数。我们从当前人口调查揭示的特殊问题中得知,截至2020年9月,大约60%的大学毕业生至少已经部分时间返回工作岗位。我们还知道返回岗位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证据仍然微弱。总有一线希望,我们的性别规范会被强制性居家工作的尝试打破,不去办公室上班的惩罚将会减少。
在一些领域,员工重返办公室的压力颇大。高盛集团的大卫·所罗门鼓励交易员返回总部。塞尔吉奥·埃尔莫蒂(Sergio Ermotti)担任瑞银集团CEO时曾表示:“如果员工待在家里,银行将尤其难以凝心聚力,创造并维系企业文化。”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CEO更以一种略嫌功利的语调指出:“不去工作场所工作的人可能会错失良机。”
尽管随着经济缓慢、犹豫和不完全地开放,样本家庭照顾孩子的总时间有所减少,但是女性承受的负担很可能未曾改变。因此,在新冠时期和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时代,样本家庭的女性花在照顾孩子及其远程教育上的总时间大约是前新冠时代的1.7倍。由于总的工作时间增加,而帮忙的伴侣有部分时间回归办公室,大学毕业的在职女性承担的总保育时间的比例从前新冠时代的60%左右升至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时代的约73%。
儿童保育分工的不平等并非昨日才凸现,劳动力市场也并非猝然经历“非升即走”的激烈竞争。确切地说,是新冠疫情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比起丈夫(或伴侣)和孩子的父亲,母亲们已经或可能将在工作和事业上遭遇更大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