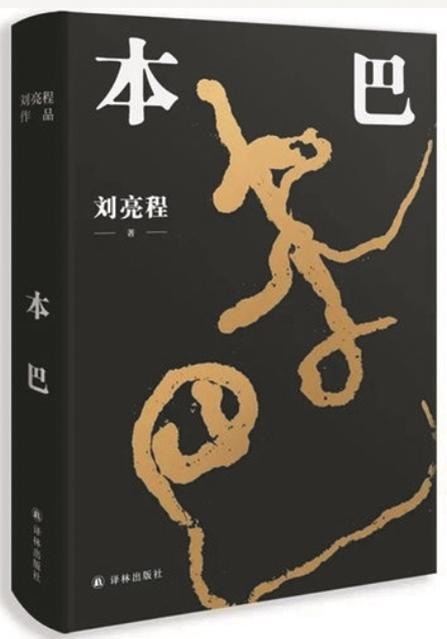
●王东
刘亮程的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本巴》,是一部充满着奇特梦境和瑰丽想象的神奇之作。书中大量的梦境描写,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类命运的象征。在本巴国度中,梦境与现实相互交织,形塑了一个既遥远又似曾相识的世界。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文艺性和批判性,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时间观念。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本巴》中的梦境是对人类历史和记忆的反思。小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追溯逝去的人类童年,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诗性智慧。这不仅是对个体记忆的反思,更是对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梦境中,本巴国度的人们通过搬家家、捉迷藏和做梦梦三个游戏,出征、转场、迁徙及东归等故事,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往返穿梭。
在小说中,游戏作为一种象征,成为连接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构的桥梁。孩子们从“母腹”带来的游戏视角,象征着他们对世界的一种纯真的、直观的理解,这种理解尚未被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所污染。而这种视角所看到的现实,无疑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批判和反思。在梦境中,人类可以对抗时间的流逝以及对衰老的恐惧。在小说中,本巴国度的人们永远停留在25岁,洪古尔停留在没有岁数的童年,赫兰不愿意长大。小说中作者描绘的这种渴望和追求,表现为对美好而不可触及的母腹的怀念,这种怀念既包括对过去的回忆,也包括对未来的期待。而这种渴望和追求,正是人类内心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它体现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和理想。在这个没有衰老和死亡、人人活在25岁的本巴国度里,作者重塑了时间。这种描绘实际上是作者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深入洞察和思考,是人类对回归起源、重获新生以及永恒存在的渴望。书中这种叙述方式,使得读者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思考人类在时间的长河中的位置。通过这本书,作者试图实现人类对时间的把握,甚至跳出时间的桎梏,实现人类的自由,而且是肉体和精神层面的双重自由。
《本巴》中的梦境是人类无法回归的故乡的隐喻。这种故乡,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本巴大草原,也包括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对故乡的追寻和怀念,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梦境中的征战、游戏、饮酒,以及穿越回现实中看到的广场上英雄的铜像,让人往往恍惚其中,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作者通过这样的叙事手法,折射出内心对时间的挣扎和反抗,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表述的那样,时间不是线性的、不是时序性的、不是空间性的,而是循环的、非时序的和生命性的。在《本巴》中,作者通过重构人类的时间感知,提出了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体现在他对史诗传统的再创造上,也体现在他对人与自然、记忆与历史等问题的深度剖析上。时间并非线性的朝向一个方向流动,人类并非只能朝着死亡前进,人类并非永远地回不去故乡。作者想让读者知道,人类渴望的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受梦境与现实的限制,人类能够永恒地活着,永恒地活在自己的故乡,从肉体到精神。
《本巴》是一部文学佳作,它不仅丰富了读者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本巴》一书的最后,作者附上了他的写作史,“一个人的时间简史——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
作者对噩梦的恐惧伴随着他从少年、青年到老年,他不打算用惊醒来从噩梦中解脱,他要把梦中的危难在梦中解决,让梦一直做下去,这也就是《本巴》的核心。而这对他在创作技巧层面来说充满挑战,在灵魂层面更要富于神奇的想象。在《本巴》中,他用一个梦套一个梦来摆脱时间的束缚,摆脱命运的追逐,回到精神的故乡,从而跳出时间,跳出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藩篱。
“我曾看见一张时间的脸,它是一个村庄、一片荒野、一场风、一个人的一生、无数的白天黑夜,它面对我苦笑、皱眉,它的表情最终成了我的。我听见时间关门的声音,在早晨在黄昏。某一刻我认出了时间,我喊它的名字。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说的时间可能不是时间。我用每一个句子开启时间。每一场写作都往黑夜走,把天走亮。我希望我的文字,生长出无穷的地久天长的时间。”刘亮程如是说。





举报成功